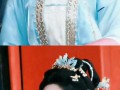加之对卵巢和乳房发育的检测结果,医生告诉张凤,妞妞的情况就是“中枢性性早熟”,她很可能出现初潮来得过早的情况,到那时给她长个子的时间就不多了,她最多还有1~2厘米的空间能长。
医生给张凤提出了两种方案:顺其自然或打性抑制针。

9岁女孩打性抑制针半年花十万
顺其自然,就是让妞妞多运动,调整饮食,早睡觉。即便来了初潮,按照自然遗传的身高,妞妞最低也能到1米55左右,乐观一点还有可能长到1米6。
而打性抑制针,就是通过长期的药物干预,抑制孩子的发育,让身高快速生长减慢,抑制骨龄过快的成熟。说得更直白些,就是让初潮的时间滞后一点,给孩子长身体的时间就能更久一点。
“按理想打满两年,要花20万元左右”
打还是不打?张凤陷入纠结。
张凤自身并不算高,157CM的她原以为找一个180CM的老公,就不会让妞妞面对身高的困扰。
回家之后,张凤拉着女儿和老公开了两次家庭会议。老公的意思很明确,“打针一定会有副作用,孩子顺其自然最好。”
妞妞态度摇摆不定,一会儿觉得爸爸说得对,一会儿又担心自己真的长不高。
张凤自己也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:高昂的治疗费用对她家来说,并不是“随时随地都能拿出的一笔小钱”;医生的一句“副作用不明确”,也让她心惊胆战。
三个月后便是做决定的时刻,依然在芭蕾舞教室。
张凤站在教室外,隔着玻璃看着女儿穿着舞鞋,自信地昂着头,跳着不标准但优雅的动作,“我不能让女儿的这份自信消失。”张凤暗下决心,不管花多少钱,这个针,她打定了。
距离妞妞打抑制针到现在,已有大半年之久。
张凤在卧室的门边贴了一张身高贴纸,从打完抑制针到现在,妞妞每个月都会平均长高一点点,有时肉眼看不出来。
看着贴纸上画满了身高的横线,母女俩会互相给对方加油打气。
妞妞爸虽然一开始不太支持,但看女儿在慢慢变好,也主动戒了甜食,家里的冰箱再也没有冰淇淋和巧克力蛋糕,取而代之的是牛奶和鸡蛋。
打针的过程是痛苦的。药物需要从腹部皮下导入体内,针头比普通针头粗上三四倍,用药量是以体重为基准算的,妞妞每个月需要打3.75mg的药剂。
打性抑制针的第二个月,张凤开始“双打”,也就是同时打抑制针和生长激素,两针加在一起一个月要花一万多元。大半年下来,检查加上来回的路费、医药费,张凤粗粗算了一下,有近10万元。按照最理想的情况打满两年,也要20万元左右。
针剂一旦开始打便不能停下,必须要定期到医院报到,这是一场持久战。
每次去医院时,妞妞都要做左旋多巴的激发试验,张凤都会听到妞妞的惨叫。
打完针,妞妞背上书包走出医院,“我想跳芭蕾舞时更好看。”
“并非所有的性早熟儿童,都需要打针”
在某网络平台,一条科普抑制针的帖子下,评论有上百条,都是纠结是否需要打抑制针的内容。
“女娃目前10岁,测骨龄11.9,预测只能长到158CM,预计10.9岁来初潮。需要打针吗?”“9岁9个月女孩,身高154CM体重75斤,骨龄11岁。乳房开始发育,还有必要打吗?”……
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群体。
从给妞妞打针开始,张凤就加入了一些打生长激素针和抑制针的家长群。张凤发现,原来有如此多的家长和她一样,愿意花几十万元来买一个“不被歧视”的身高。
“一个月粉剂要五千块,要是换成水剂,就更打不起了。”一名家长在群里吐槽道。这里的粉剂和水剂,指的就是生长激素。
家长们举出梅西靠打生长激素长到170CM的例子,殊不知梅西是因为11岁时的诊断是:缺乏生长激素导致的侏儒症。
“家长们其实是不管这些的。如果医院不让打,他们就会在群里说,能不能去私立医院找找门路。”张凤说,她自己也接到过很多家长的来电咨询。
张凤挨个告诉家长,妞妞不是别的原因,确实是被诊断为中枢性性早熟才打针的,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诊断。
“如果医生不建议打,去哪里可以打到这个针?”妞妞围棋班的一个家长陈灿向张凤询问。
张凤记得陈灿和她的孩子,陈灿本身不高,每次来接孩子,都穿着高跟鞋,梳着高马尾。
张凤不明白,为什么自己反复纠结要不要打的针,在陈灿那里就变成了非打不可。